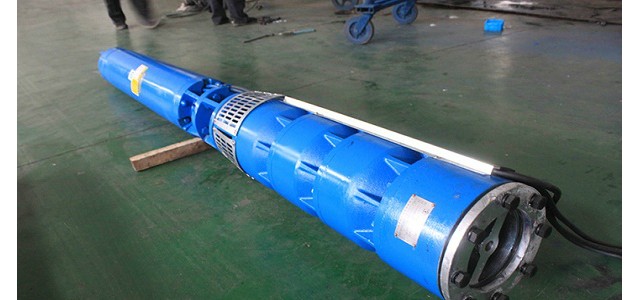我小的時(shí)候,我家在農(nóng)村,莊園占地特別大,每年到春天的時(shí)候,父親特別愛(ài)栽樹(shù),因此我家房前屋后長(zhǎng)滿(mǎn)了各種各樣的樹(shù)。有一次,我發(fā)現(xiàn)在我家屋后的草堆旁,不知何時(shí)長(zhǎng)了一棵小樹(shù)。我第一次注意到它時(shí),我就好奇地問(wèn)父親:“爸,咱家屋后種了不少桃樹(shù),這一棵樹(shù),也一定是桃樹(shù)吧?”
父親看了看那一棵小樹(shù),分辨了好久,硬是沒(méi)有分辨出來(lái)。父親說(shuō),也許是一棵梨樹(shù),但似乎又不像。我不禁對(duì)這棵樹(shù)有了強(qiáng)烈的好奇心。于是,只要有人來(lái)我家,我便多了一件事,那就是,問(wèn)他們是否認(rèn)識(shí)那棵樹(shù)。
一天,正在林業(yè)大學(xué)讀書(shū)的表哥來(lái)我家,我趕緊把表哥拉到那棵小樹(shù)邊,我問(wèn)他:“這棵樹(shù)你該認(rèn)識(shí)吧?”他審視了一會(huì)兒,說(shuō):“這是一棵櫻桃樹(shù),你看它的葉子,就是櫻桃樹(shù)的樣子。”終于知道了這棵樹(shù)的名字,而且是讀林業(yè)大學(xué)的表哥確認(rèn)的,這應(yīng)該不會(huì)錯(cuò)。從此以后,只要有小朋友來(lái)我家玩,我都會(huì)興奮地告訴他們說(shuō):“過(guò)幾年我就有櫻桃吃了,我家的那棵樹(shù)是櫻桃樹(shù)。”
就這樣,過(guò)了四年,那棵櫻桃樹(shù)慢慢長(zhǎng)大。就在我上初中的那一年,它開(kāi)花了。看它開(kāi)了滿(mǎn)樹(shù)的花,一天晚上我放學(xué)回家,父親高興地把我拉到屋后的那棵小樹(shù)邊,高興地說(shuō):“孩子,今年你有李子吃了,你看這棵李子樹(shù),花開(kāi)得多好。”
“爸,這是一棵櫻桃樹(shù)。”“別傻了,櫻桃樹(shù)什么樣子,我能不知道嗎?咱家的這一棵是李子樹(shù)。”想不到,被我叫了四年的櫻桃樹(shù),原來(lái)是一棵李子樹(shù)。
李子樹(shù)花開(kāi)花落,幾粒微小的青果開(kāi)始顯現(xiàn)。就在我等著吃李子的時(shí)候,一場(chǎng)大風(fēng),讓樹(shù)上看得見(jiàn)的幾粒微小的果子不見(jiàn)了蹤影。很長(zhǎng)一段時(shí)間,我都沉浸在懊惱當(dāng)中。
因?yàn)樯狭顺踔校乃拊趯W(xué)校,那棵李子樹(shù)漸漸淡出了我的視野。花開(kāi)花落又一年,一天我放學(xué)回家,母親笑著對(duì)我說(shuō):“屋后的那棵棗子樹(shù),終于結(jié)棗子了。”明明是一棵李子樹(shù),母親怎么說(shuō)是一棵棗子樹(shù)呢?
見(jiàn)我不信,母親拉著我的手,來(lái)到屋后,用手指著樹(shù)端的幾粒青棗說(shuō)。那兒確實(shí)掛著幾粒小小的青棗,原來(lái),我們家屋后的那棵樹(shù),既不是一棵桃樹(shù),也不是梨樹(shù),更不是櫻桃樹(shù)或李子樹(shù),它是一棵棗樹(shù)。
如今十多年過(guò)去了,老家的那棵棗樹(shù)早已長(zhǎng)成了參天大樹(shù)。每次想起這棵棗樹(shù),我的心中總涌出許多感慨。想不到,這棵棗樹(shù),被我們張冠李戴,最后還是它用幾粒果子,證實(shí)了它的真實(shí)身份。
在我的人生成長(zhǎng)中,我一直記著這棵棗樹(shù),它讓我明白了一個(gè)道理,一個(gè)人在成長(zhǎng)過(guò)程中,就像一棵不知名的樹(shù),有時(shí)候要弄清楚你到底是一棵什么樹(shù),必須等到你奉獻(xiàn)出自己的果實(shí),等你功成名就后,別人才會(huì)認(rèn)識(shí)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