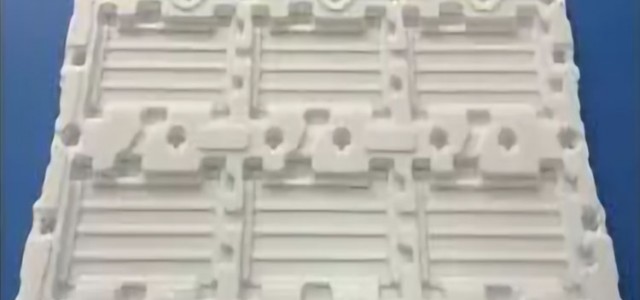穿過鏡頭 回到家鄉(xiāng)
雷釗的爺爺和奶奶。受訪者供圖
返鄉(xiāng)的方式有很多,雷釗靠的是攝像機(jī)。
6年前,這位武漢大學(xué)新聞傳播學(xué)院廣告專業(yè)的畢業(yè)生,鉆進(jìn)他的老家——山東省德州市齊河縣雷莊村,拍出一部紀(jì)錄片《爺爺奶奶的村莊》。
這只是華北平原上一個最普通的村莊。村子里28戶人家的600多口人中,幾乎一半都是留守老人。他們每天的活動無非是按部就班做頓飯,拿鋤頭在院里的菜地遛上一圈,繞著村子散散步,對著電視盯一會兒,或是搬上馬扎坐在門口瞇眼曬太陽,天一黑就窩在屋子里等著進(jìn)入夢鄉(xiāng)。
與2019年春節(jié)前的紀(jì)錄片《四個春天》不同,雷釗表示,《爺爺奶奶的村莊》并沒有那么強(qiáng)的故事感,也沒有激烈的沖突。幾乎所有他拍到的素材,多半的時間里都被平靜和無聊充斥,“這就是留守老人們的日常生活”。
雷釗本來并不熟悉這樣的日常。他也曾像很多年輕人一樣,邁著大步越走越遠(yuǎn)。他兩歲半就離開雷莊村,跟著父母搬到山東德州市城里,大學(xué)開始這些年,他還去了法國、尼泊爾,一畢業(yè)當(dāng)過北漂,如今留在了距家鄉(xiāng)千里之外的武漢。
他越走越快,家鄉(xiāng)的時間軌跡卻近乎靜止:磚頭拼接成地面,白墻已經(jīng)發(fā)黃摻進(jìn)了黑點,木屋頂?shù)酱查g被一塊釘住的木板簡單地隔開,上了年頭的平房就是爺爺奶奶大部分的活動空間。
這個原本只有暑假和過年才偶爾邁進(jìn)老家的年輕人,決心再一次走進(jìn)村莊,記錄老人的真實生活。他一個人承包了導(dǎo)演、攝像和剪輯工作。常常支起三腳架,打開攝像機(jī),雷釗就發(fā)現(xiàn),面前的老人已經(jīng)抹起了眼淚。
這些留守老人有的面臨農(nóng)村的典型矛盾,幾個兒子纏在家產(chǎn)爭奪里,來看老人的次數(shù)屈指可數(shù)。也有人抱怨,家已經(jīng)拾掇好了,(孩子)也不回來住。
爺爺在村里走著,指著路邊堆滿稻草的房子:“東西都壞了,兒子在外面,屋子也毀了。”
一個老人的屋子修了7遍還漏雨,一條裂縫從墻頭拐到墻根,門也差點砸掉了。老伴的遺像就掛在墻上,她獨居多年,看著附近一家接著一家搬走,房屋被雜草纏繞,淚水止不住往下流。拍完,她怯生生地拋出一句,“明天再來啊孩子”。隔天,她又想刪掉自己的鏡頭,怕兒子看到。
這是這些老人們生活里常見的片段。根據(jù)2016年民政部初步摸底排查結(jié)果,全國有1600萬左右的農(nóng)村留守老人。作為城市化進(jìn)程中被遺忘的部分,他們必須要掌握的功課是應(yīng)對“孤獨” 。
在雷釗看來,一輩子生活在農(nóng)村的爺爺奶奶對“城市化”沒有宏大的概念,他們的感受是直觀而具體的:樓變高了,年輕人少了,這里的年味不濃了。
在老人逐漸老去的這些年,雷莊村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,大量人工耕種被農(nóng)業(yè)機(jī)械代替,通上了水電,路邊從零星的自行車、摩托車,變成了面包車和小轎車,附近村莊的老人相繼住進(jìn)樓房,能聊天的人也少了。如今,村里撤了小學(xué),年輕人離去,搬到縣城或城市安家。
“就像兩條跑道,年輕人在這一條狂奔,他們在自己的路上緩緩行駛,似乎沒想去追趕,最終漸行漸遠(yuǎn)。”雷釗說道。
紀(jì)錄片拍攝花了3年左右。那時候,在雷莊村,手機(jī)上網(wǎng)絡(luò)信號只顯示為“E”,雷釗常常“失聯(lián)”,空閑時只能靠看電影和看書消遣,正如他所拍到的素材一般“平靜和無聊”。
雷釗的爺爺奶奶都已經(jīng)80多歲。除了勞作,爺爺偶爾寫些毛筆字,也做手工,家里的掃帚、炊帚是他折騰出來的。至于奶奶,似乎沒什么愛好。
能讓他們?nèi)计馃崆榈模敲恳粋€“特殊的時間節(jié)點”:春節(jié)了,兒女回來了,孫輩結(jié)婚了。
在雷釗的記憶里,多數(shù)老人很少主動撥通兒女的電話,但等待是常有的——有人會在兒子常回來的那天,默默到胡同口站一個上午,也經(jīng)常不自覺地念叨:“他們什么時候回來?”
爺爺奶奶的身體也一天天變差。拍攝的3年時間里,雷釗發(fā)現(xiàn),爺爺已經(jīng)走不了太遠(yuǎn)的路,活動的范圍從全村縮到了家附近。奶奶的耳背越來越嚴(yán)重,聽不清就點頭笑著應(yīng)和。她會捋著頭發(fā),盯著鏡子沉默半晌:“小孩兒是越長越好,老人越長越難看啦。”
他們分別生過幾次病。天轉(zhuǎn)涼了,爺爺套了8層衣服,把自己裹得鼓鼓囊囊。奶奶包著頭巾窩在床上,褶皺遍布的手,鄉(xiāng)村醫(yī)生找打針的血管費了半天勁兒。
眼睛看不清了,再看電視,他們就搬著板凳挪到屏幕前,直愣愣地看著《動物世界》里的斑馬遷徙;忙活一陣兒停下,一把漏著洞的二胡被爺爺緊緊攥在手上,坐在屋里吱嘎吱嘎地拉著不知哪里聽來的小曲兒。家里要裝新煙囪了,爺爺小心翼翼地爬上半米多高的梯子,在窗口拉鐵絲、釘釘子,不小心把奶奶的手弄破了道口子。
拍完了片子,爺爺奶奶也開始把雷釗掛在嘴邊念叨。如今,隔上幾個月,他會回到這個村莊,在屋里陪他們待上一會兒。
兩個老人嫌他離家太遠(yuǎn),不過沒勸他回來;他們不了解做導(dǎo)演到底是干什么,但笑呵呵地和其他老人解釋,“這是給你們錄像哩”;他們多數(shù)時間已經(jīng)習(xí)慣沉默,能和雷釗說起的,也只有問問冷暖,或是扯到回憶。
他們都老了。走在田里時,一架飛機(jī)飛過,爺爺嘟囔著,“這飛機(jī)怎么還會放炮”。
要過年了,爺爺親手寫下春聯(lián),其中一句是“知足心常樂”,他把它貼在了大門上。
告別夏天來到冬天,這是雷釗鏡頭里又一年的春節(jié)。熟悉的小院子突然被年輕人和小孩兒塞滿,門口的汽車停得滿滿當(dāng)當(dāng),大家排著隊拍了全家福,在院子里笑著跑來跑去,這個家里終于有了點兒生機(jī)勃勃的感覺。
表針就要走過零點,電視里開始為新一年倒數(shù),這是一年里最熱鬧的時刻。年輕人成群結(jié)隊地跑到門外放鞭炮,只剩下兩個老人守著老舊的電視機(jī)。一切又慢下來了,沒一會兒,他們在屋里自顧自地睡著了。
記者 王景爍 來源: